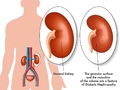横石河畔癌症村 珠江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修复实验
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但这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自从作为环境致病的极端个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上坝村就成了环境学者们实验土壤修复技术的最佳地点。
根据2004年9月全国第二次农业土壤普查:上坝村农田中的锌、铜、镉、锰等重金属严重超标,其中铅超标44倍,镉超标12倍。
修复这样的土壤,使它回到被污染之前的状态,使时光倒流、回到从前,是学者们试图实现的理想。
广东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提到日本经验,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把危险的含镉土搬出耕地,换上安全健康的土壤。这种方法最简单,但最有效也最昂贵,要维护食品安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难以找到可供替换的土壤,日本也实验出一套生物方法,他们尝试了近两百种水稻种子,找到了一种有超级吸收重金属能力的水稻。平均1千克水稻秸秆,能吸收70毫克镉。但缺点是,种出来的米不能吃,要扔掉。秸秆可以送到生物能源所试验发电。
这些方法无疑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然而,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陈能场也在上坝做水稻吸收重金属的实验,那些富含镉的秸秆,被送到广州能源所,再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转化为能源。要用水稻把所有土壤里的重金属吸收殆尽,花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农民看来,这种方式显得奢侈。
学者们又琢磨新办法,把广钢的硅渣变成硅肥,施种在水稻田里,希望借此减少水稻对重金属的吸收。
这些复杂的实验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上坝村非常欢迎学者们把这里做成能源实验基地,村治保主任何寿明的任务,除了骑着摩托车照看水渠、修水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陪同专家学者,每隔一两个月来照看他们的田地。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初夏的团队也把上坝选为实验基地,他们在这里种相思草和甘蔗。实验证明,这两种作物能够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存活,而且能吸收重金属,植物可以用来制酒精或者发电。
这是一个从科学和社会效益上都站得住脚的方案,但是农民心里有自己的账。比如能源作物,种甘蔗,送去提炼酒精,如果没有补贴,就很难在上坝村推行,村干部说,甘蔗200元一吨,果树900元一吨,谁愿意种甘蔗?
没有政策引导,学术研究也没有发展到商业化种植,村民仍然吃自己种的稻谷,尽管这些稻谷镉超标若干倍。
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如果不看横石河水,上坝村真像是鱼米之乡。早稻收割的季节,满眼望去金黄的谷子铺在路边上,太阳暴晒下,可以闻到清甜的香味。上坝的龙眼很好吃,西瓜水分多,而且甜。它本来是广东粮仓的一部分,现在成了被污染到极致的典型。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和农业的污染问题,珠江流域有多少粮仓正在默默承受污染?
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土壤调查曾显示,珠三角近四成菜地重金属超标,导致蔬菜中铅镉残留较多。在强势的工业面前,农业往往是弱势的被污染,农民是默默地承受。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年轻人都希望努力读书,考出这个村子,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今年上坝村又有两个孩子考上了本科线。其中一个是邱新凤的孙女,她的父母因为癌症早早去世,让她比别的孩子多了一分老成。
癌症又轮到何宝成身上。何宝成以前是个壮汉,患了肝癌后,瘦骨嶙峋。他没有放弃治疗,吃了很多药,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他从小喝井水,吃土里长出来的粮食,不知道该怪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横石河原来是一条大河,深得可以人头朝水跳下去,触不到底,那时横石河很亲近。上世纪80年代后,水土流失,矿渣陆续抬高河床,河水浅的地方可以赤脚趟过。再往后,横石河越来越可怕,所有人都想远离它,连在这里投资水电站的老板都自认倒霉摊上了它。
污染很容易,但要让小河重新变清,井水重新变甜,土壤没有毒,要让时间流转,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倍于污染的成本。
村民最现实的想法是,引水渠能加上盖子,再加固,真正为村子送来干净水,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人心思定。
要彻底解决,一是换土,一是换水,两种都不可能,上坝村村支书何来富说,搬迁也不可能,农民靠什么生活?我们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实习编辑:谢瑜琳)
- 网友评论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