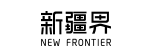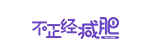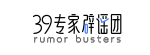11月16日 小雨
今天,妈妈转院,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舒缓病房”。
妈妈已经昏迷10多天。“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你换个安静些的地方,让她平静地睡去吧。”三甲医院的管床医师劝说。
见我收拾东西,病房众人都来打听。听闻是去“舒缓”,直言:“那去等死咯。”
我想解释几句。终究,只是呵呵两声,快步走开。
我前两天去实地咨询,也曾有这种感受。
那时,医生未等我介绍病情,开门见山:“‘舒缓病房’除了镇痛,不做其他任何治疗。你能接受吗?”
“我妈已经不治疗肿瘤。她现在血压有点高,后续用些降压药……”
“我们不使用医疗手段,刻意延长生命。懂我意思吗?”医生说。
我跑了3家“舒缓病房”,都被回复“不治疗、不输液、不打针”。
这和我想得不一样。
一般,临终关怀不再对疾病本身,进行干预。但,用点降压药,不让患者因高血压而头晕;用些化痰药,避免患者憋痰憋气——我问医生,这为什么不算“对症治疗、减轻痛苦”?没有作答。
(作者注:事后发现,“不治疗”会因情况而异。下文有述。)
我没有心理准备,“什么都不做”。于是,又去了其他医疗机构求床。包括区中心医院、街道医院,及N家护理院。
有的说:“我们没有癌症患者要用的药。没法收。”
有的正值冬季住院高峰,楼道都塞满床。
有的看完病史资料,抖起二郎腿:“你是打算,让她死在这里?不过也没法带回家,总归不吉利……”
有的同意接收,但只能用TA们的护工,家人不能陪夜。其6人间的病房内,两张床仅一臂之隔,没有床围和帘子。一个老奶奶仰面躺着,下身没有任何遮盖。约莫1分钟后,1名护工拿着尿布进屋。全程,另1人站在门口,啃黄瓜。
我用了三四天,寻找、思考。最终,决定转入“舒缓病房”。
原因有三。
一是环境。“舒缓病房”是小间格局,一屋就2或3张床,内有绿植、挂画。窗外是高高的玉兰树。窗下有个小花园。咨询当日是个晴天,床上铺开一整片阳光。楼道里有谈心室、告别室。这里更像养老院,而非医院。
二是“私密空间”。1名护工对应3名患者,优于护理院1:6、1:7的配制。
据病友家属说,护工一般不守在病房里。
那么,拉起床帘,我那些在三甲病房没机会说的话、碍于面皮不曾流的眼泪,就有了出口。
三是,我几次咨询“舒缓”,都在24小时内得到回复:“你母亲的生存质量评分很低……我们安排她明天入院……”
我上网搜索肿瘤患者生存质量评分表。对应妈妈的现状,测评结果是:卡氏(KPS)评分,20分;体力状况(PS)评分,4分;生存质量(QOL)评分,<20分。
从这些分值推断,妈妈活得很辛苦。
如果用各种方法,只是让她在痛苦中度日,这是害是爱?
几夜不曾合眼后,我决定遵照妈妈的意愿,“不折腾,舒服地离开”。
11月17日 晴转多云
妈妈的邻床阿姨,肺癌骨转移,不到60。
她一刻不停地呻吟:“哎哟……痛呀……儿子……”
给她擦身。毛巾角垂下、撩过其胸口,阿姨身体顿时一缩,“哟哟,别擦了别擦了。”
家属几次打铃,向护士站求助:“拜托,还有什么办法嘛!”
约莫五六分钟后,医生来了。TA拍拍阿姨肩膀:“***,哪里疼?”
“轻一点……我全身都疼。”
“止痛贴、口服药都用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医生站在床边,对着家属,如是说。
再接着,医生稍做检查,请家属“隔壁聊聊”。回屋时,家属鼻头泛红。
这天下午,护士拿来一个小音箱:“听音乐伐?能分散注意力。痛得厉害,也可以给她揉揉。”
“碰着就疼,没法揉。”其儿子脱口而出。
护士摇摇头,离开了。
循环播放的音乐,夹杂着阿姨的哼哼,没有静心,反感烦躁。
还有几次,阿姨的丈夫想按铃、请医护。被他儿子阻止,“叫来也没用。算了。”
“舒缓病房”似乎没有获得家属信任,没有成为其面对亲人死亡时的“帮手”。
这天晚些时间,护士叫我到谈心室:“后面的事,你要准备起来。”
“哦……护士,真到那天,会是什么样?”我的脸鼓成包子,长出一口气后问。
护士抬头看我,眼神却没聚焦。“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妈妈可能是一口痰堵住,也可能是突然的心肺衰竭……我们会观察的。手机24小时要保持畅通。”
从这天开始,我失眠了。
11月18日 小雨
妈妈,我错了。
我不该掰开你的嘴,把手指头伸进去,还掏掏掏,妄图把那口痰挖出来。
我一定弄痛你了吧。瞧那眉头皱的。
但你不能咬我呀!出血了喂!
我今儿没碰到医生。明天,我一定再来早点!医生或许有办法,把你那口浓痰弄干净!
11月19日 多 云
一早,隔壁间和我妈邻床都空了。
护工说,今天是邻床入院第四天。“她儿子守了3天,没留住。”
而隔壁间的爷爷,前一天还能自己坐起来,就着家人的勺子,吃两口干饭,吐槽医院伙食真不行。
我突然想起,妈妈入住当天,医生问完病史后,主动提出:“她肺部有些湿啰音,整体状态还行。你们想用点抗生素吗……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她有静脉置管,输液也方便……”
这有悖于我最初听到的“舒缓病房不治病”的规定。
然后,TA喃喃自语:“也不能每次来,两三天就没了。”
于是,自入住舒缓病房起,妈妈每天会用抗生素和抗癫痫药。
这也是治疗我的药,疗愈我走出“无能为力”的抑郁期,接纳疾病和现状。
11月20日 多云转晴
我趴在妈妈床边码字,一位五六十岁的男性拍拍我:“小姑娘,这是你的谁?”
“我妈。”
“你们什么毛病?你们输的什么药?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坚决不输液……”
“叔,您问医生吧。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医生每天查房吗?这里医护怎么样?”
“医生办公室在楼上。”我默了一会儿,答。
连日来,我和医生共照面5次:第一天我去登记病史时,医生来做入院心电图时,第二、三天去询问情况时,第二天临床阿姨打铃时。
我每天约8点半到院,下午4点半离开,未能赶上查房。也甚少见医生主动进病房询问情况。
我愿意将此理解为,医生不想打扰病患和家属。
“有事可以打铃。”我上楼找医生,会听到如此叮嘱。
这没有宽慰到我,没有让我感觉被支持。
当我问“妈妈还好吗”,真正想知道:她是趋于平稳,慢慢走向衰竭,还是已到弥留之际?
我希望医护能在那个时刻来临前,提醒我,“这两天守着她,别走。”
回想6年前。爸爸离世前几天,监护仪持续报警。医生着急忙慌给我打电话:“这两天,家里人不能走,很危险。”氧饱和降到80时,医生说:“哪些人必须在场?快让他们来吧。”
而这一次,“舒缓病房”没有监护仪,我无从得知妈妈的生命体征。
怎么办?
离开病房时,我贴在妈妈耳朵边说:“宝贝儿,乖乖的,明天我们再见。”
我希望这是一句咒语,赐予我俩力量。
11月21日 雨
(内容补记于2018年11月29日)
清晨5时许。手机震动了。
陌生来电。坚持不懈地响着。
我坐直,深吸一口气,接起。
“***家属,你妈妈5点钟没了。你大概多久到医院……”
嗡嗡嗡嗡嗡嗡嗡。我脑子炸了,机械地回应着电话。
赶到医院时,妈妈仰面平躺,还没擦拭、更衣。她脸色微黄,五官舒展,神情淡然。脸颊温温的。
“我前半夜,给她掏好几次痰……后来,我睡熟了。梦里面,好像听不到齁齁的痰声。我吓醒了,一摸,你妈妈已经断气。”护工说,“半夜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想到你的小孩……”
因着护工的好心,我没能和妈妈告别。
我陷入极大的愧疚和自责中。
我已经无从得知,妈妈在临终之际,是否有片刻清醒?她会不会害怕、孤单?她有没有唤我的名字?如果我出现,抱一抱她,她会笑吗?哪怕是看她流泪也好。
我甚至无从确认,妈妈辞世的准确时间。
我提出,能不能送妈妈去“告别室”,给我们从容道别的时间和空间。哭成翔,也不会影响其他人。
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我后槽牙咬得紧紧,不让自己哭出声,给妈妈擦拭、更衣、整理妆容。
其间,护士来为妈妈撤除管子。TA两次更换钳子,细细地找切入口,只为不剪伤妈妈的皮肤。
但床帘还没来得及拉好,操作就开始了。这和我需要的“尊重遗体”,不一样。
邻床新病友为避嫌避晦,始终背对我们,斜靠在窗边。进入“舒缓病房”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预料到结局。但让将死之人目睹别人的死亡,听到别人的哀嚎、痛哭,会不会太残忍了?
“小姑娘,你别太难过。你妈是解脱了。”护工劝说。
从抵达医院,到送妈妈上灵车的5个小时里,这是我从“舒缓病房”工作人员处,收获的唯一安慰。
39健康网(www.39.net)专稿,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

 39健康网
39健康网 早晨5点,妈妈走了……
早晨5点,妈妈走了…… 亲人癌症晚期,治疗还是放弃?一位医生为患癌父亲选择了最少治疗
亲人癌症晚期,治疗还是放弃?一位医生为患癌父亲选择了最少治疗 上海首家临终关怀病区:不是慢性安乐死,让生命带着尊严"谢幕"
上海首家临终关怀病区:不是慢性安乐死,让生命带着尊严"谢幕" 老人肺癌晚期如何护理
老人肺癌晚期如何护理 一个年轻医生,和他的临终患者口述史
一个年轻医生,和他的临终患者口述史 肺纤维化临终关怀怎么做
肺纤维化临终关怀怎么做 预计每年服务700-1000人次,广州成立首个面向儿童的安宁疗护项目
预计每年服务700-1000人次,广州成立首个面向儿童的安宁疗护项目 老人肺癌晚期,儿女执意抢救后痛苦离世:癌末期,有必要治疗吗?
老人肺癌晚期,儿女执意抢救后痛苦离世:癌末期,有必要治疗吗? “种植一口牙相当县城买套房” 种植牙集采要来了 能降多少?
“种植一口牙相当县城买套房” 种植牙集采要来了 能降多少? 想想都痛!女子健身房上私教课腿骨被压折,如何避免运动中受到伤害?
想想都痛!女子健身房上私教课腿骨被压折,如何避免运动中受到伤害? 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情况,霍乱是什么病?
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情况,霍乱是什么病? 还有这等好事?研究发现多照镜子或有助减肥!
还有这等好事?研究发现多照镜子或有助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