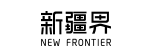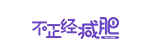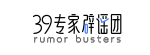患病几年来,深圳的Andy到过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医问诊,而且排除的不仅仅是艾滋病,还包括甲肝、肺结核、各种性病等等疾病。
而和他一样有过类似求医经历的人大量存在。他们还给卫生部部长写信,向病毒研究机构求助。他们的目的一致:他们想要弄明白,他们是否感染艾滋病变异病毒?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未知病毒?
身体上的“症状”,让他们无法相信专家们做出的“恐艾说”。他们认为“恐艾说”的结论“简单而不负责任”。
但对于这些反复检测HIV抗体的人,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临床专家们的观点几乎一致:他们肯定没有感染艾滋病。专家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最高卫生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个人群的判断。
因此,两者之间观点的冲突,使得这个人群更为焦虑。
并非感染艾滋“看不到他们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体征”
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专家蔡卫平从病理上分析,这个人群并非感染艾滋病。
“他们所说的症状是持续很久的,而且发病很快,所以这些症状虽然和艾滋病有些相似,但是和艾滋病发病期完全不一致,艾滋病只有发病期、急性期才有一些症状,其他阶段基本上没有症状。”蔡卫平说。
蔡卫平还称,目前,基本上不存在抗体检测不到的情况,虽然有极少数人某一次检测不到,但那与自身免疫能力有关,并非永远检测不到,而“他们用很多方法检测了很多次,有的人既检测了抗体,又检测了病毒,所以不可能检测不到”。
“即使艾滋病有变异也不会这么早发病,也有无症状期,还要经过免疫确诊,而他们的免疫指标都很好,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病?这是偏执型心理障碍。”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浙江省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时代强说。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恐艾症”人群,往往把自己的病症和艾滋病对号入座,“跟艾滋病相似症状的病多了,别的病也可以降低免疫力”。
C D 4和C D 8是人体两种免疫细胞,其数值的高低,和两者比值的大小,是判断人体免疫力的重要依据,而中外CD 4正常值标准不一,即使国内的不同地区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如国外一般为800/m m3到1000/m m 3,中国湖北正常平均值为690/m m 3。
蔡卫平称,CD 4在500/m m 3以上属于正常,350/m m 3到500/m m 3是轻度异常,350/m m 3到200/m m 3之间是中度异常,而在恐艾人群中,几乎都是正常或轻度异常。
中国政府规定,当艾滋病人的CD 4小于200/m m 3时,国家才会免费发放药物。而桂希恩临床发现,“恐艾症”人群没有这么低的,都在300以上。“这只能说明他的免疫力比正常人差一些”。
“心理障碍,精神高度焦虑,都可以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继而出现很多症状,引起免疫力低的疾病很多,不能说免疫力低就是艾滋病。”时代强说,“血常规不正常、淋巴细胞总数偏低,和艾滋病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艾滋病可以产生所有的症状,但产生类似症状,并不一定是艾滋病。”
为了减少类似人群的精神焦虑,杭州第六人民医院从三年前就引进国际最先进的H IV抗体检测试剂———第四代酶联,这可以将排除艾滋病感染的时间提前到四周。
而我国普遍采用三代酶联试剂进行检测,而且从可能感染病毒的时间算起,三个月后检测的结果阴性才算排除。
“很多人熬不到三个月就已经精神崩溃了,也有人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了。”时代强说。
桂希恩、李太生、蔡卫平、时代强,以及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生吴炎,都是国内艾滋病治疗领域权威专家,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个人群所主诉的症状,并不构成医学意义上真正的症状。
他们说发烧,医生测量没烧;他们说舌苔白,医生认为是精神过度紧张后引起的内分泌失调;他们说淋巴结肿大,医生说,全身两个部位以上、直径1厘米以上、持续3个月以上的情况,才叫持续淋巴结肿大,“他们摸到的浅表慢性炎症引起的淋巴结可能是肌腱”;他们说皮疹,医生说,没有一个人的皮肤没有瑕疵;医生体检时也没有发现有临床意义的皮疹。
“医学上,病人主诉很重要,但一定要有真正的体征,但是看不到他们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体征。”李太生说。
求助研究机构“病人”们并不接受专家的“恐艾”之说
医生诊断要有三个依据:一是主诉(病人陈述),二是看体征,三是客观检查。
李太生曾经累计跟踪过40名类似病人,并对他们的免疫值做了实验室检测。
他发现,40%的人C D 4确实偏低,但是CD 8不高,只有3人CD 8稍微高一点。而艾滋病感染者,不管窗口期、急性期、临床无症状期、艾滋病期,99%以上的人CD 4可能早期是正常,CD 8一定要高于正常,而这些人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他还给他们做了C D 8激活亚群的检测,但指标也不高,这不仅排除了艾滋病,还排除了其他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同时又能在血液中活动复制的病毒感染的可能。
“忧郁症的病人,CD 4也会低,恐艾是个严重精神问题。”李太生说,“而少数人的CD 8偏高,这不排除别的病毒感染。”
李太生早在1997年,于国际上首先提出艾滋病病人的免疫功能重建的新理论,这一科学发现为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在艾滋病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太生称,他系统观察的40人,也不会感染未知的病毒。“真要是新病毒,我肯定会研究下去,我还想拿个诺贝尔奖呢”。
在这些专家之间,“恐艾说”几成定论。
时代强、吴炎等人均称,他们每年都要接待数千“恐艾症”病人。早在2007年,李太生就撰文称,这个数目庞大的人群,以及愈来愈多的社会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困扰着临床工作者。
而那些艰难“求生”的“病人”们,也早已找过这些国内的权威了,但是他们并不接受专家们的“恐艾”之说,甚至在网上谩骂专家。
“现在的医生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拿着高工资。事物都是发展的,病毒也在变化,不能简单用已知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洪生说。
于是,他们又通过Q Q群,发动集体的力量,寻找研究机构,主动把自己提供给他们研究,或者向国家卫生部这样的权威机构求助。
2008年,一个叫做“港湾”的Q Q群,被腾讯公司解散,原因是病友们组织起来给国家卫生部打电话、写信,甚至组织病友去北京“上访”。
去年6月份,一个叫做“出路”的Q Q群,组织了两批共20名病友,从全国各地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免费检测H IV。
不过,这次检测并不是以中心的名义,而是以中心下属的一个实验室的名义负责的。实验室与每个人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明确告知,这是实验室行为,不收费,经费由实验室自筹,检测结果仅供参考,不具有临床诊断价值。
“单位不会出面做这个事情,即使要做,也要交给门诊,由门诊实验室做临床检测,而他们早在别的医疗机构做过临床检测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我们实验室做。”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部的助理研究员万延民说。
这并非一个贸然的决定,因为从2007年开始,就有很多类似病人打电话,或者邮件联系该中心。该实验室认为,此事具有探讨的必要,他们想研究是否真有艾滋病新病毒,或者新的病原体感染。
万延民透露说,第一次,实验室给2名病人做了检测,发现不是艾滋病,就不想再做了,但是更多的病人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也觉得第一次人少。会不会也有一部分人真的有新病毒感染,所以又有了第二次检测”。
“他们还是怀疑H IV感染,要求我们做H IV抗体检测,而我们实验室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因此我们只为他们做H IV抗体检测,没有发现异常。”万延民说,“我们做完H IV检测以后,又把血样交给中心另外一个做未知病原体检测的研究团队,但他们也没有发现别的病原体感染迹象。”
结果显示,这20人中,除了2人查出结核病外,其他人都正常。
想被研究不容易难以立项,“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因此,万延民也认为,心理因素是这个人群致病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新的病原体感染,我接触了一些朋友,说他们完全是恐出来的,似乎也解释不通”。
但要对这个可能的“未知病毒”进行研究,限制因素太大了,最重要的是经费问题。
“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下做检查,很麻烦,实验室检测项目会很多,要占用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万延民说,“而没有明确的课题立项,没有国家项目固定支持,很难有实验室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做这个事情。”
一个研究课题的立项,须先做研究计划,再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立项,再拨款,科研机构才有钱做研究。
但万延民称,这种情况立项很难,“虽然这些人诉说的症状很明显,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所以,写课题申请书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方向,专家在评审时很困难,就会提反对意见。而且预期的成果是否能拿到一个明确的病因?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研究,投入很难有产出,因此很难立项”。
蔡卫平也认为,研究机构直接受理这个人群求助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未知的病原体感染远远多于已知的,找不到病因的情况比找到的机会还多。而研究机构不掌握临床,因此,他们的研究必须和临床机构联系一起的,“SA R S在确诊之前,临床怀疑是呼吸道引起的,研究机构就在呼吸道系统找,还找了很久才找出病因。临床可以缩小研究的范围,使得研究的成功几率增加”。
桂希恩、时代强等专家在提出“恐艾说”后,遭到谩骂,之后,他们言语变得谨慎而周全了。
时代强称,不否认他们可能有其他疾病,那只能从其他方面检查排除,也不否认可能有未知的病毒,但在没有诊断之前,只能对症治疗,减轻症状,减轻痛苦。“有的病人吃了我们开的抗焦虑的药就好了”。
“我也不排除他们可能有其他性病或者未知病。对不了解的东西也可以进行研究。”桂希恩说。
蔡卫平、李太生的观点则更为鲜明。
“如果他们确实感染新病毒,医学界一定很感兴趣,但他们全部没有医学意义上的病症,谁会去找(病因)啊。得有个头绪,到底是哪类东西感染了?如果是感染的话,得要有客观的指标。”蔡卫平说。
李太生的措辞激烈:“谁会把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只有主诉,没有体征,客观检查也没有不正常。这除了精神病和心理障碍,没有别的病。”
桂希恩认为,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障碍。对这个人群应该给予帮助和关心,“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伤害很大”。
“恶性循环”“群里的病友95%都有过高危行为”,开放的性是问题根源?
北京地坛医院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但还是从外面聘请了一位心理专家。因为心理医生不懂艾滋病,艾滋病医生不懂心理学,精通两者的医生很少。
然而,收效甚微。
“因为这个人群人太多了,每个病人都不能通过一两次咨询就可以解决的。”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生吴炎说,“而且病人也不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精神障碍。”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认为,对恐艾人群的关心,需要各个领域协作,精神卫生学、心理学、性学、社会学等等都要参与进来,“但我国性学、精神卫生学、心理学都发展得太慢,20年来没什么进步”。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主要开展艾滋病教育、性的研究与教育等等。“爱知行”也没有设置针对恐艾人群的部门。
“他们都会来找你,而且会反复找你,会把你搞崩溃。”万延海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表示,目前,除了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没有任何组织面对恐艾人群。她建议,可以由志愿者,或者其他民间组织,甚至是真正的H IV感染者,在得到政府承认、专家机构培训和协助情况下,对恐艾人群进行心理的疏导。
蔡卫平在描述这个特殊群体时,使用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词:因为有了“高危”性行为,所以在身体出现一点病症时,开始恐艾,但在反复检测呈阴性时,又怀疑感染了未知的病毒,这导致精神的极度焦虑,因此免疫力降低,继而出现更多的病症,这又增加了恐惧……
39健康网(www.39.net)专稿,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

 “师徒传带”下西藏县级医院首例胸椎内镜手术成功开展
“师徒传带”下西藏县级医院首例胸椎内镜手术成功开展 特别的教师节礼物!肝病专家骆抗先教授收到一幅油画
特别的教师节礼物!肝病专家骆抗先教授收到一幅油画  中国抗癌协会:共同打造肿瘤防治融媒体生态
中国抗癌协会:共同打造肿瘤防治融媒体生态 周宏伟:用检验医学打造健康新标靶
周宏伟:用检验医学打造健康新标靶 在医院看病,专家号和普通号有什么区别?哪个时间段看病比较好?
在医院看病,专家号和普通号有什么区别?哪个时间段看病比较好? 医疗系统的“大众点评”来啦!南方医疗就医平台今日上线
医疗系统的“大众点评”来啦!南方医疗就医平台今日上线 怪妈妈跟老师透露了隐疾,高三男生一气之下选择辍学
怪妈妈跟老师透露了隐疾,高三男生一气之下选择辍学 金域医学“爆雷” 员工涉疫被立案!检测能力不够?样本丢失?数据造假?
金域医学“爆雷” 员工涉疫被立案!检测能力不够?样本丢失?数据造假? 想想都痛!女子健身房上私教课腿骨被压折,如何避免运动中受到伤害?
想想都痛!女子健身房上私教课腿骨被压折,如何避免运动中受到伤害? 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情况,霍乱是什么病?
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情况,霍乱是什么病? 还有这等好事?研究发现多照镜子或有助减肥!
还有这等好事?研究发现多照镜子或有助减肥!